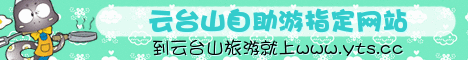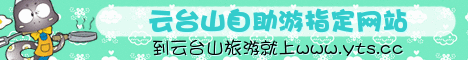公元262年8月,伴随着一曲《广陵散》,嵇康走到了生命的终点。
嵇康死后,竹林七贤其他人的命运和归宿又是如何呢?
嵇康被杀后,向秀在家中闭门沉思。
不久,他来到洛阳,叩响了大将军府的大门。
据说,当时司马昭正在与臣僚在府中议事。
《晋书》本传记载:见到向秀,司马昭故作惊讶地问道:“闻君有箕山之志,何以在此?”
传说尧帝要让位给巢父、许由,他俩不接受,就逃到箕山隐居,因此,箕山之志就是隐居之志。
向秀回答:“巢父、许由是狷介之士,不理解尧帝的一番苦心,不值得钦慕和效法”。
向秀的这番回答,司马昭听了非常高兴。
从此,向秀走入仕途。先后担任过“散骑侍郎,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”等职。
因为是不得已而出仕,向秀只是做了一个“朝隐”之士。《晋书》本传说他:“在朝不任职,容迹而已。”
一个寒冷的黄昏,向秀路过昔日与嵇康、吕安等人聚会的山阳旧居。
伴随着远处传来的清越高远的笛子声,向秀迈着沉重的脚步,慢慢地走近曾经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。
故地重游,触景生情,向秀又仿佛看见了嵇康、吕安等人的身影。
272年,嵇康被诛杀后的第十个年头,四十五岁的向秀在忧郁中离世。
向秀的墓地就在他的家乡附近。虽然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侵蚀,墓冢依然醒目。
嵇康被杀后,阮籍依然每天以酒为伴。
263年的10月,曹髦死后继任皇位的小皇帝曹奂,被迫加封司马昭为晋公。阮籍知道,司马昭迈出了这一步,离改朝换代的日子就不远了。
一个叫郑冲的官员提议,《劝进表》由大名士阮籍执笔。
最后,派去的人在袁孝尼家,找到了醉酒酣睡的阮籍。原来,他只顾喝酒,竟把这件事忘到了脑后。
来人赶紧叫醒阮籍,说《劝进表》等着急用。
其实,阮籍心里不愿意写《劝进表》。想用醉酒的办法搪塞过去,但是,他心里明白,这一次是躲不过去了。
于是阮籍带着醉意,伏案疾书,一气呵成,写好了《劝进表》。
司马昭看了《劝进表》后,满心欢喜,愉快地接受了封爵。
写了《劝进表》的一两个月后,在一个寒冷的夜晚,五十四岁的阮籍,在痛苦、失望、忧郁、自责中离开了人世。
临终之前,阮籍又想起与朋友们聚会的那片竹林 ,想起了自己作的那首咏怀诗:
一日复一夕,一夕复一朝。
颜色改平常,精神自损消。
胸中怀汤火,变化故相招。
万事无穷极,知谋苦不饶。
但恐须叟间,魂气随风飘。
终身履薄冰,谁知我心焦。
阮籍去世两年后,265年8月,司马昭病死。
四个月后,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逼迫曹奂退位。然后,率领文武百官在洛阳南郊设坛祭天,举行了隆重的“受禅”典礼。
司马炎登帝位,改国号为晋,建都洛阳,史称西晋。
随着司马炎登基,竹林七贤中的山涛,官也越做越大。后来,他终于当上了司徒,成为早年梦寐以求的三公。
山涛为官清廉。他虽然身处要职,但与家人一直住在只有十几间屋子的旧房里。
283年秋天,七十九岁的山涛得了一场大病。不久,就去世了。
死去的山涛叶落归根,安葬在他魂牵梦绕的家乡。
山涛在世的时候,曾经在司马炎面前,推荐过竹林七贤中的阮咸。
走进官场以后的阮咸,还经常弹琴长啸吗?还潇洒地饮酒吗?在始平太守的职位上,他又有何建树?因为史料的欠缺,这一切都不得而知。
在《晋书•阮咸传》的结尾,知道他“得以寿终”。
《晋书》本传说竹林七贤中的刘伶:“澹默少言,不妄交游,而机应不差。”
同向秀一样,嵇康被杀害后,刘伶也被迫走进了仕途,当上了建威参军。但是,他依旧嗜酒如故。
刘伶整日喝酒,不谋其政,每当朝廷询问时,他总是以无为而治来搪塞。
最终,司马炎把他罢黜免职。
据有关资料记载,罢官后的刘伶并没有回到老家安徽,而是和妻子在河南获嘉县境内、黄河岸边一个叫桑古寺的地方,开酒店做起了生意。
“桑古寺”靠近古驿道,加上刘伶酒名远扬,善于经营。因此,他开的酒店每天宾客盈门、生意兴隆。
随着刘伶的后代繁衍兴盛,“桑古寺”曾一度叫做“刘伶村。”后来,又更名为刘固堤村。
大约在公元300年,八十岁的刘伶病逝。
刘伶死后安葬在刘固堤村东北方向约一公里的地方。
公元305年,王戎病逝,享年七十二岁。
《晋书》本传记载:王戎生前也到过昔日与嵇康、阮籍等人聚会的地方重游,并对陪同他的人发出这样的感叹:
我过去与嵇康、阮籍曾经在此畅饮,共为竹林之游。自从他们两个逝去,我便为时务所羁绊了。今日旧地近在眼前,当年的事情却邈若山河了。
西晋以来,嵇康、阮籍成为名士的楷模,名声日盛。
东晋之后,人们将嵇康、阮籍等人的清谈游赏称之为“竹林之游”。
专家考证,大约东晋时已经有“七贤”的称呼了。
东晋时期,玄学理论走上没落之路,而凸显的仅仅是玄学外化的形式——纵放狂诞的生活态度与行为。因此,人们对玄学的抨击也多着眼于此。
东晋思想家、医学家葛洪对此批评道:“世人闻阮嗣宗傲俗自放,古人所谓‘通达’者,谓通于道德,达于仁义耳。岂谓通于亵渎而达于淫邪哉!”
鲁迅指出:因为他们的名位大,一般的人就学起来,而学得无非是表面,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。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,于是社会上便有了很多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。
到了东晋,一些有识之士对西晋覆灭的教训,进行认真的反思。
认识到了仕不事事,也就是在其位不谋其职,以及放荡无度的生活态度带来的极大危害。
纵观历史,对于竹林七贤,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。
对竹林七贤持否定意见的人们,有的站在儒家之学的立场上,批评他们崇尚道家虚无思想,致使圣人之学沦丧;
有的站在维护教化的立场上,批评他们放荡无羁,破坏了纲常 ;
还有的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,批评他们中的某些人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,以致清谈误国等等。
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,倾向于把西晋灭亡、甚至魏晋禅代的原因,直接归之于竹林诸人。他说:
“正始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,一时名士风流,弃经典而尚老庄,蔑礼法而崇放达,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,即此诸贤为之倡也。自此以后,竟相祖述。”
鲁迅指出: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,人云亦云,一直到现在,一千六百多年。
尽管历史上对竹林七贤评价不一,但从两晋南北朝一直到清代的一千多年间,竹林七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,他们宏放旷达的精神风貌、生活情趣或行为,一直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有着巨大的影响。
1960年5月,南京地区西善桥南朝大墓里,出土了《竹林七贤与荣启期》画像砖。
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,其作为与七贤颇为相似,因而被放在了一起。
在画像砖上的七贤,有的抚琴啸歌,有的颌首倾听,有的高谈玄理,有的舞弄如意,人人宽衣博带,孤傲高雅;崇尚老庄之情,追求个性之心,溢于画面。
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,在画像砖上得到充分的表现。
这些砖画出现在皇亲国戚的陵墓中,清楚地表明,当时社会上层对魏晋玄学的推崇,以及对竹林七贤的景仰。
据《续高僧传》记载:有一位南朝后梁的僧人,非常景仰阮籍,其生活态度也颇似名士。
南北朝之后,嵇康的历史形象渐渐定型。
在后人的歌咏中,他钟情山水,饮酒弹琴,不受羁绊,不肯随俗,桀骜不群。成为高士形象的代表。
杜甫在《入衡州》一诗中写道:
我师嵇叔夜,世贤张子房。柴荆寄乐土,鹏路观翱翔。
白居易也在一首诗中写道:
张翰一杯酣,嵇康终日懒。尘中足忧累,云外多疏散。
陆游在《自嘲》一诗中吟唱道:
华子中年百事忘,嵇生仍坐懒为妨。病于荣宦冥心久,老向端闲得味长。
似水流年,经过历史长期的沉淀,阮籍的人格形象,已经演变为“离经叛道”的人格典型,成为一种特定的思想文化形态,并影响着后人。
在魏晋士人中,鲁迅先生特别推崇嵇康。
嵇康正直、刚毅、高傲、反叛,不肯随俗。在他身上,鲁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1913年,鲁迅开始重新修订《嵇康集》。
他历时二十多个春秋,参考多种版本,经过数十遍的校对,终于使《嵇康集》有了一个相当精善的本子。
鲁迅校订《嵇康集》以及对魏晋时代研究的重视,从整体上提高了对嵇康的评价以及魏晋思想、文学的地位。
时光飞逝,斗转星移,今天的人们该怎样评价和看待魏晋时代的“竹林七贤”呢?
为了维护封建统治,儒家提出、设计了一整套的礼制法度,并推行相关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。
但是,如果将它们强调到极端,陷于僵化的境地,就会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束缚,使人们丧失自我,丧失独立的人格。
魏晋时期,随着玄学的兴盛,以嵇康、阮籍为代表的思想家,借助于先秦道家的思想形式,重新肯定了个体层面上的人的自我意识,找到了失落已久的个性自我。
可以说,嵇康的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,在本质上显示的,是一场个性解放的运动。
当然,竹林七贤的思想和生活态度也有极为消极的一面。他们中的一些人,片面地强调自己的个性,而忽视了人在社会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。
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认为,包括阮籍在内的玄学哲学,作为立国之道,作为治国安邦的学说,是很难行得通的,是没有实效的。
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,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也往往如此,竹林七贤自然也不例外。
时光越千年,但是,他们仿佛还没有走远。
可以肯定的是,已经被人们谈论了上千年的竹林七贤,今后,仍会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被关注的一个群体。
|
云台山旅游服务网发布信息时间:2012/3/11 9:37:14
|
|
|
 |
信息查询 |
 |
|
 |
云台山旅游住宿推荐酒店 |
|
 |
云台山旅游住宿特价客房 |
|
 |
云台山旅游景点 |
|
本页已浏览次
|